https://prosyn.org/jFC5r8Bzh
New Comment
Email this piece to a friend
Contact us
Please select an option
Please wait, fetching the form
Please wait, fetching the form
Please wait, fetching the form
Please wait, fetching the form
Please wait, fetching the form
Please wait, fetching the form
Please wait, fetching the form
We hope you're enjoying our PS content
To have unlimited access to our content including in-depth commentaries, book reviews, exclusive interviews, PS OnPoint and PS The Big Picture, please subscrib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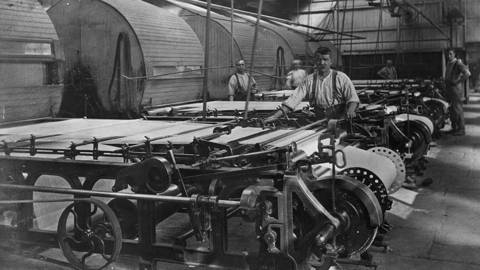
为什么神经学家、分子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和发展生物学家—这些以科研成果永久地改变了我们对自身的认识的男性和女性—对他们的未来却如此彷徨不安?这场发生在当今医学科学家之中的士气危机不是由资金问题造成的,也无关该领域所处的发展阶段,更不是因为研究水平,而是因为这些科学家们没有能够在研究过程中结成合适的人道社团。
士气低落的问题缺乏善意和体面;这是习俗和礼仪的失败,是社会目标的缺失,是辨别对错以采取正确行动的能力或意愿的减弱。归根结底,士气低落只是一个后果,其原因是终日忙碌在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们的漠然使得其研究领域的社会和情感基础日渐衰败。
以人类的身体和精神为研究领域的科学的脆弱性在于科学家们所承担的义务,即必须冷静地观察其各自的系统。在这些领域中,要做到冷静就需要医学科学家们忽略他或她个人在身体或精神上的脆弱性。试图达到这种对自身命运冷静的好奇心的不可实现的标准所带来的压力,使得这些研究身体和精神的科学家和他们自己的身体及精神之间的距离变得难以承受。在这样的压力下,医学科学家们容易产生幻想,认为他们的研究工具和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将他们从自身的精神和身体局限中解脱出来。
对这种幻想的有意识阐释是对生物死亡确定性的一种痴迷的回应:即一个信念,认为这种在科学游戏中取胜的重大意义能使胜利者获得某种形式的永生,从而战胜死亡本身。将这种通过科学发现优先获得科学永生的概念和这种更深层次、更古老和完全非科学的幻想区分开来的只有一层薄之又薄的否认的隔膜。
虽然当今的生物医学号称是在寻求对自然缺陷的修复之道,但其众多从业者的所作所为却似乎表明他们了解自然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优先获得神话般的永生,而不管自己或他人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否认对死亡的恐惧和被抑制的超越自然的愿望是在暗中创造一种生物医学的标志。而这种科学的实质与其宣称的目的相互矛盾。
问题不是科学和医学有意回避对治愈方法的探寻;而是它们被一种非理性的、治愈死亡的无意识需要过分驱动。这种动力完全来自于次要的预防和治愈疾病的任务。这项任务的目的只是为了延缓病人不可避免的生命终结,并由此延缓科学家们自身不可避免的死亡。这些由科学家和医生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做出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使对死亡的否认制度化了。
Subscribe to PS Digital
Access every new PS commentary, our entire On Point suite of subscriber-exclusive content – including Longer Reads, Insider Interviews, Big Picture/Big Question, and Say More – and the full PS archive.
Subscribe Now
但这些承诺是不可持续的。例如,一种人道的生物医学承认其目的不是超越人体的局限,因而也就不再会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除此之外,能够承认其操作中存在无意识因素的科学,只要这种无意识不存在于其研究方法中,就最有利于其从业人员作为人类大展拳脚,也最能够为我们其他所有人创造具有长期价值。
如果科学家们自己不能抽出时间考虑他们自身的行为给彼此造成的影响,那么这种变化就不会出现。我们可以从一种最为保守的方式开始这种改变,即通过对我们所持有的教授头衔的意义进行再思考。“教授”这一动作有多层含义:公开确认;宣布或宣讲;提出主张;佯装;宣称拥有某方面的技能或知识;确认某方面的信仰;接纳某种宗教信仰或组织;或发誓皈依某种宗教或组织。
除了在这些现行的含义中选择外,我们还可以从回归这一名词最初的意义开始,即中古英语的“professen”,意思是宣誓。除非教授们愿意花时间公开地肯定一些超越其研究数据的东西,否则他们就配不上这一头衔。
确认和发誓不依赖于数据;它们发自内心。在我看来,作为一名教授首先要有对自己具有重要性的东西需要确认,然后就必须去确认它。直到他们承认最强烈的情感和最佳科研数据都是决定职业行为和专业地位的因素之前,从事科研的教授们的士气会仍然低落。